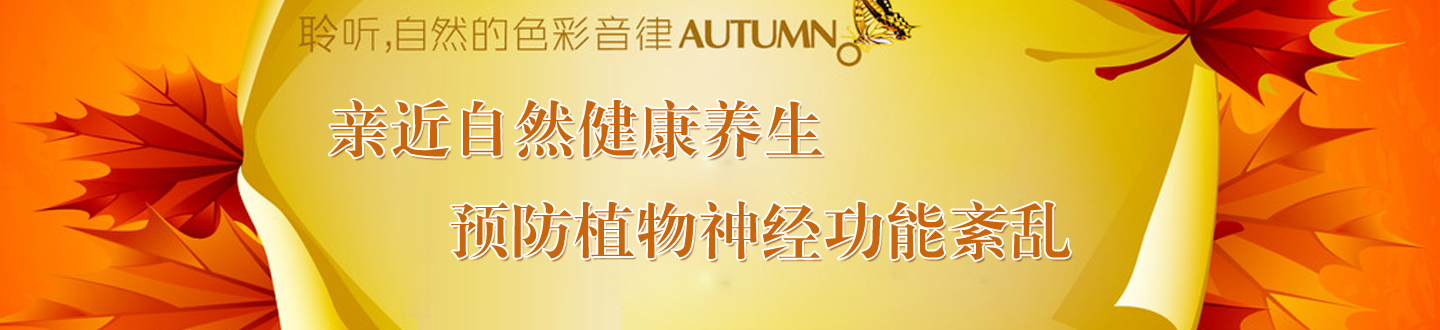
从古至今,死亡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面对死亡,很多人会表现出无奈和恐惧。虽然传统文化不鼓励我们去谈论死亡,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在临死之时才会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一事实。几乎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时刻,都会突然意识到生命必然走向死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否会因此而焦虑?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还能意识到死亡的不确定性,当这种意识与生存本能地结合在一起时,便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死亡焦虑(deathanxiety)。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死亡焦虑的内涵和特征有待被深入挖掘。探索和了解死亡焦虑的本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开展生命教育和临终关怀。
1 死亡焦虑具有内隐性
一方面,人们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死亡,这是最令人痛苦和恐惧的;另一方面,死亡又充满了未知,令人焦虑不安,人们不确定自己何时以及如何死亡,也不知道死后的世界如何。因此,人们可能对死亡同时存有恐惧和焦虑。北美护理诊断协会将死亡焦虑定义为个体因意识到死亡的存在或面对临终而感到不安、忧虑和害怕的状态[1]。Harmon-Jones等[2]认为,死亡焦虑是指面对死亡这一事实和濒临死亡而产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和焦虑。据此,笔者把死亡焦虑界定为:对即将到来的或终将到来的死亡这一事实产生恐惧、焦虑、不安等一种复杂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心理状态。
死亡焦虑的表现有外显的和内隐的两种。笔者倾向于把外显的死亡焦虑称作死亡恐惧(fearofdeath)。死亡恐惧是指意识到自己或他人终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害怕死亡或死的过程。死亡恐惧很容易因为死亡提醒(mortalitysalience)而被激活。死亡提醒是指由于个体 那些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死亡焦虑或不愿意直面死亡焦虑的人,虽然没有体验到明显的死亡恐惧,但却常常通过压抑、否认、隔离、转移或替代等防御机制来逃避和应对死亡焦虑。有些人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限制,不敢轻易改变现状;有些人则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名誉、性和权力等。也有很多人通过高冒险行为来排解死亡焦虑,或通过在暴力的电子游戏中体验“二次生命”来征服死亡。Popham等[3]认为,有些年轻人试图通过一些充满活力的经历以使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进而认为自己不会衰老,也许这样做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与死亡拉开了距离,进而更好地面对死亡焦虑。
IrvinYalom[4]在《直视骄阳》一书中指出,死亡焦虑通过隐藏和伪装,转化成各种症状,它正是我们所体验到的诸多困扰、压力和内心冲突的源泉。也就是说,死亡焦虑常常改头换面成一系列貌似与之并不相关的症状或问题,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人们身上:对疾病的恐惧,对健康状况的过度 在人的一生中,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始终存在,根植于我们的心灵深处。特别是在各种灾难性事件面前,都不难发现死亡焦虑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有许多事件可以诱发死亡焦虑,如丧失至亲的人、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或遭遇重大创伤,或只是单单思考这些事件也会引起死亡焦虑。“当灵车驶过,也许下一个就是我?”可以说,所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也都有自己应对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的方式。
对死亡的恐惧伴随着人的一生。从孩童时期开始,我们便会注意到死去的动物、过世的祖父母以及慢慢衰老的双亲。进入青春期,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很多青少年会开始思考死亡这个主题,少数人偶尔还会产生自杀的想法。有些青少年通过讲述死亡笑话、观看恐怖电影或从事高冒险行为等来缓解死亡焦虑。很多人在退休之后,效能感和自我价值迅速下降,变得容易失眠,死亡焦虑也随之上升。到了晚年,如果个体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平静地接受死亡,那么其死亡焦虑会明显增加。
早在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就认为,痛苦来源于我们对死亡无所不在的恐惧,一个人最大的忧虑和恐惧就是对于死亡的忧虑和恐惧[5]。死亡的必然性与不可预知性使得人们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一种根本性的焦虑,对其他焦虑障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没有指向的焦虑往往是死亡焦虑的表现形式[6]。有些人体验到明显的死亡焦虑,甚至陷入死亡恐惧之中而无法享受活着的欢愉。而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焦虑虽然没有直接呈现在意识中心,但它却会转换成各种心理疾病,如出现反复就医的躯体化障碍,或是没有具体指向的广泛性焦虑症等。相反,人们不会认为死亡焦虑是其他心理问题的伪装。
死亡焦虑是很多焦虑症患者的主要问题。如果患者有严重的焦虑症(不直接表现为死亡焦虑),那么治疗师就要考察其是否有死亡焦虑。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死亡焦虑存在正相关,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一般也有较高水平的死亡焦虑[7]。惊恐障碍其实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死亡恐惧。那些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者、照顾慢性病人者以及长期生活在医疗环境中的人,他们的死亡焦虑程度比其他群体要高。当然,也有些人虽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但并没有经历着严重的死亡焦虑,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
对于很多人来说,衰老也是焦虑的一大来源。“变老”意味着身体机能的退化,意味着正在加速失去曾经拥有的健康、优势和一些能力。衰老还提醒着人们死亡即将来临。可见,很多害怕衰老的人,心里并不是真的害怕自己老去,而是怕死。研究表明,衰老焦虑和死亡焦虑存在较大相关,衰老焦虑是死亡焦虑的一个预报器,担心衰老也是死亡焦虑的一种表现[8]。
3 死亡焦虑具有不可消解性
既然死亡焦虑具有普遍性,那么该如何化解死亡焦虑呢?有些人相信来生,相信灵魂不死;有些人通过孕育后代而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永生;有些人通过努力工作,发挥潜能,创造成就,名垂青史而获得永生,等等。
许多宗教信仰给人们提供了“永生”的机会,创造如相信生命轮回或灵魂不死等文化世界观来减轻死亡焦虑。毫无疑问,宗教信仰安抚了许多人的死亡焦虑。Morris等[9]通过对基督徒、穆斯林以及无宗教信仰者的死亡焦虑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基督徒的死亡焦虑得分显著低于穆斯林和无宗教信仰者,穆斯林的死亡焦虑得分显著低于无宗教信仰者。但是,宗教信仰只能解决死亡恐惧,并不能彻底消除死亡焦虑。
Zhou等[10]的研究发现,生育子女可以减轻和缓解死亡焦虑,他们认为婴儿是死亡的对立面——新生,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感、成就感和价值感,并提升父母的自尊水平,从而相应地降低死亡焦虑。孩子的成功也会给父母带来荣耀。父母经常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研究表明,与有生育子女的成人相比,无生育子女的成人常常缺乏一种生活满足感[11]。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千方百计地想自己生育一个孩子,为什么中年丧失独子给人造成的伤痛和打击会那么大。但这也只能说,相比无生育子女的成人来说,已生育子女的成人的死亡焦虑相对较低。有人通过生育孩子来缓解和对抗死亡焦虑,但死亡焦虑并不会随着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而得到彻底的消解。
Tomer等[12]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死亡焦虑的一个综合模型,该模型认为,有两种方式可以减轻和缓解死亡焦虑:减少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遗憾,以及使死亡有意义。过去的遗憾指个体本应该实现一些抱负却没有实现而存有的遗憾。未来的遗憾是指随着生命的衰老或过早的死亡,一些愿望没能在将来得以实现而存有的遗憾。如果个体感到有很多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遗憾,或者觉得死亡没有意义,那么他们就会体验到较高的死亡焦虑。个体过去的遗憾少,表明其应该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异小,没有什么应该完成而却没完成的目标。个体未来的遗憾多,说明其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异就较大。而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都会存在差距。更何况,现实自我、应该自我和理想自我都容易因受到个体观念的转变而改变。如果认为死亡是有意义的,或者体验到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那么其死亡焦虑就较低;相反,若把死亡看作是无意义的或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则其死亡焦虑就会较高。但有研究发现,虽然寻求人生的意义与死亡焦虑存在显著相关,但这种相关并不大[13]。寻找到生命的意义或死亡的意义,可以帮助人们减轻死亡焦虑,然而并不能彻底消除死亡焦虑。
高自我实现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潜能,对人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对实现未来的愿望也有极大信心,因而与低自我实现的人相比,他们的死亡焦虑更低。低自我实现的人对人生充满悔恨,过去的遗憾多,为没有实现本应该实现的目标而感到愧疚,这种愧疚感进一步增加了死亡焦虑。也就是说,越是觉得没有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死亡恐惧越明显。然而,自我实现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过程,不存在一种最终的自我实现状态。这样来看,追求自我实现只能减轻死亡焦虑,而不能彻底消解死亡焦虑。
虽然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死亡焦虑和克服死亡恐惧,但都无法彻底消解死亡焦虑。不管是通过生育后代、信仰来生,还是通过创造性的成就来获得所谓的永生,这些最多只能驱除死亡恐惧,而不能从根本上消解死亡焦虑。
4 死亡焦虑具有两面性
“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些死亡的画面,人死了一定很可怕吧?会痛吗?世事难料,如果我突然死去,该怎么办?会不会给亲人带去巨大伤痛?整天纠缠在这一大堆死亡问题之中,心神不安,工作也漫不经心。”网络上随处可见这类与死亡恐惧或焦虑相关的案例。在临床治疗中,通过深入分析,常常发现有很多心理障碍都与死亡焦虑有关,而如果没有挖掘出患者对于死亡的焦虑,那么治疗往往事倍功半。当一个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存在与必然性时,就容易体验到一种生命的无意义感,并激发出强烈的焦虑与恐慌——死会让我们失去一切。
当死亡焦虑严重时,个体还可能会出现冒冷汗、肌肉紧张、恐慌不安、呼吸急促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虚度人生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的死亡焦虑来自于从未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没有充分地活出真实的自己,觉得还从来没有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你觉得人生还未圆满,还有很多事情未完成,那么你的死亡焦虑也会越高。
虽说直面死亡会引发焦虑,但死亡意识也可能成为觉醒体验,引发重大的积极改变。直面死亡有时能够引发戏剧性的长久改变。“癌症治好了神经症”,很多人在面临巨大死亡威胁时终于领会了生命的意义,知道该怎么活,很少担心被拒绝,不再对他人感到恐惧,从而摆脱了神经症的折磨。死亡焦虑唤起了人们寻求意义的强烈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地评价自我,自我追问如何过一种充实的生活。
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关系,尤其是感情的联系。每个人都需要与其他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死亡焦虑可以让我们积极地去建立联结,尤其是人际联结,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生活在一种紧密的关系中。换句话说,人际联结对于安抚有死亡焦虑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不仅存活于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将生命传递下去,波动影响到下一代,甚至代代相传。
由此可见,死亡焦虑具有两面性,程度恰当的死亡焦虑对于个体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它促使个体更加珍惜生命,避免危险行为,努力发挥潜能。为了消解死亡焦虑,一个暂未自我实现的人将可能极力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积极采取行动以避免更多的遗憾。但是,如果死亡焦虑过于严重,则会使人神经衰弱,限制人格的健康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既然死亡焦虑无法彻底消解,那么我们就不能让生命被死亡所冻结,而应该直面死亡焦虑,就像正视其他焦虑或恐惧一样。直面死亡,可以让我们更加爱惜生命,尽力发挥潜能,迸发创造力,过一种更加充实和富有同情心的生活,让我们既存有死亡焦虑而又不为其所困。如果死亡焦虑能够引发重要的人生转变,那么,我们就要去探究在日常的生活模式中如何去引发这种转变,而不是让个体在面临巨大的死亡威胁时才意识到这种转变。
参考文献
[1]杨红,韩丽沙.死亡焦虑及其量表的研究与发展[J].医学与哲学,,33(1A):44-46.
[2]HarmonJonesE,SimonL,GreenbergJ,etal.Terrormanagementtheoryandself-esteem:Evidencethatincreasedselfesteemreducesmoralitysalienceeffects[J].JPerSocpsychol,,72:24-36.
[3]PophamL,KennisonS,BradleyK.AgeismandRisktakinginYoungAdults:EvidenceforaLinkbetweenDeathAnxietyandAgeism[J].DeathStud,,35:-.
[4]亚隆.直视骄阳[M].张亚,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9.
[5]肖剑.西方古典思想中的“死亡”意识:从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到塞涅卡[J].思想战线,,35(2):71-75.
[6]FurerP,WalkerJ.DeathAnxiety:ACognitiveBehavioralApproach[J].JCogPsychot,,22(2):-.
[7]MartzE.Deathanxietyasapredictorofposttraumaticstresslevelsamongindividualswithspinalcordinjuries[J].DeathStud,,28:1-17.
[8]BentonJ,ChristopherA,WalterM.Deathanxietyasafunctionofaginganxiety[J].DeathStud,,31:-.
[9]MorrisG,McAdieT.Arepersonality,well-beinganddeathanxietyrelatedtoreligiousaffiliation?[J].MentHealthRelCult,,12(2):-.
[10]ZhouXinyue,LeiQijia,MarleyS.etal.Existentialfunctionofbabies:Babiesasabufferofdeath-relatedanxiety[J].AsianJSocPsychol,,12:40-46.
[11]WismanA,GoldenbergJL.Fromthegravetothecradle:Evidencethatmortalitysalienceengendersadesireforoffspring[J].JPerSocPsychol,,89:46-61.
[12]TomerA,EliasonG.Towarda重庆治疗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医院哪家比较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mwoao.com/zlff/6522.html